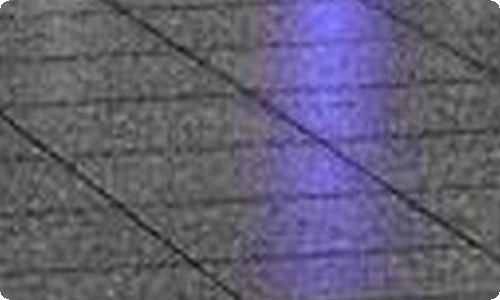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
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,提到睡衣出行,最早受到关注的是上海。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,上海依然保持着一些老传统,包括一些很土的习俗,比如“穿睡衣出门的上海人”就一直顽强地存在,以下分享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。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1
在魔都,一年四季,你都能看到一些居民喜欢穿着睡衣出门溜达……
这是魔都特有的“魔性”吗?
说起来令人有点费解:“穿睡衣出门”——这种看起来有点“不文明”的行为,在上海这样数一数二的大城市,居然还挺常见的。
对于“穿睡衣”出门这种行为,你是否看得惯?
这是不雅的“陋习”,还是无可厚非的个人习惯?
在上海,咱们时常能看到一些居民穿着睡衣在公共场合晃:街上压马路啦,公园里散步啦,菜市场买菜啦……在这座城市里,各种五颜六色的棉睡衣无处不在,让许多刚来的人挺懵X的:上海好歹是中国最现代化、最时尚的大都市,咋有这么多本地人如此“不文明”呢?
十年前,当我刚来上海时,我也一度十分懵X。我一直以为这种“睡衣现象”只在欠发达的地区才有,比如我老家。那是湖南的一座小城市,很多人都喜欢穿着睡衣出门溜达。
但令我意外的是,上海居然也是一样一样儿的。地铁上,穿粉红色麻布睡衣的大妈和穿职业正装的年轻人挤在同一节车厢里,这奇妙的画面咱也是司空见惯了。
不过,很多人都觉得在公共场所穿睡衣,这既不合适也不礼貌。虽然“城市是我家”这句标语大家都听过,但最初这是用来号召大家不乱扔垃圾的,不是让你穿着“家里的衣服”在外面随便晃的嘛
然而,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了,我也逐渐了解到了上海人对于睡衣的那份独特喜爱。这背后还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原因的呢。
现代的西式睡衣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。早在20世纪初,当国外的睡衣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,它们可是昂贵的奢侈品,只有上海本地的富人才穿得起。有一套好看浮夸的睡衣,穿着出去溜达溜达,那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象征。至于普通老百姓?他们不穿睡衣出门,可不是因为不好意思,而是根本穿不起啊。
当然咯,现在的睡衣便宜多了,大家也都买得起了,但在一些老上海人眼里,在外面穿睡衣还是蛮潮哒!就算不“潮”,但至少无可厚非。
更何况,现在很多睡衣还是蛮好看的。你如果去南京路步行街或者新天地逛逛,那里一些人穿的睡衣可是高端大气上档次,制作精良颜值高。想想优衣库卖的一些睡衣,长得和咱们平常穿的休闲运动服也没啥区别嘛。就连香奈儿、纪梵希等大牌,也曾设计过“睡衣风”的服装,价格还颇为不菲。
某种程度上,睡衣甚至成了本地的某种时尚标志,集休闲、艺术、个性与怀旧于一体。在去年的上海秋冬时装周,一些模特就特意穿着睡衣去石库门拍写真,向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致敬。
不过,魔都的“睡衣文化”也引起过当局不满,他们认为这有损于上海的大都市形象。十年前,在2010世博会即将召开时,上海一度尝试禁止居民穿睡衣出门。
“齐八小区的文明着装劝导队每周活动两次。他们……衣着整齐地立在小区门口,看到有穿睡衣的居民要走出小区,志愿者便会上前劝阻。”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09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。
文章里说,如果有居民抱怨这些志愿者管得太多,志愿者就会劝道:世博会时,外国人参观完园区出来以后拿着相机到小区乱窜,很有可能到我们小区来……不能给上海丢脸。
上海注重脸面,这可以理解。但是……区区睡衣而已,老外会那么在意么?早在2008年,美国摄影师Justin Guariglia就在上海大街上拍过许多穿睡衣之人的照片,还为此专门出版了一本书。
在《华尔街日报》2008年的采访中,他是这样说的:“这(穿睡衣出门)主要是一种上海的时尚现象,很有魅力也很优雅。虽然当地媒体对于‘居民该不该在外面穿睡衣’有过激烈争论,但我是支持这一举动的。也希望在世界范围里,有更多人可以接受它。”
我个人不会穿睡衣出门。不过,其他人在街上穿自己喜欢的任何衣服,我都觉得无所谓。西方文化里有“休闲星期五”的传统,员工们在周五时可以想穿什么穿什么,上海也可以借鉴下这种传统啊~ 不过上海的版本估计得叫“裤衩子星期五”啦。
希望上海不要再限制居民的着装了。魔都是开放、包容而多元的——这种“包容”和“多元”不仅仅对于外界,对本地的人民也应是如此啊。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2
上海人为什么喜欢穿睡衣出门?这是一个和上海有关的名话题。
上海作家马尚龙认为,话题的关键词不是“睡衣”,而是“上海人”。
“大家似乎对上海人有一种刻板印象,觉得上海人就应该穿西装出门。结果外地游客到上海来,看到满大街的睡衣,难免要谈论几句。”
在马尚龙的印象中,睡衣曾经是上海的一个符号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绽放无比。
然而,在居住空间的巨变中,上海的“睡衣文化”正在消失。
那些过去住在弄堂里的阿姨爷叔们,带着不舍得丢弃的旧睡衣,随着拔地而起的新房越住越远。
一件小小睡衣的兴衰史,这背后其实是半个世纪以来上海人居住空间升级变迁的历史。
穿行于上海街头的睡衣一族,总能让人一眼辨认出来。
上海“睏衣”解析图
它有几个标志性的特征。
首先,必须是一套头,统一式样的衣服加裤子,经典的小碎花款式是主流。
衣服两侧一定要有口袋。夏天的男士睡衣还要多一个袋,位于左胸处,用来放纸币、手表、打火机。
冬天的睡衣多半要搭配上更加花哨的罩衫、袖套,防尘防脏。
其次,衣服的袖口和领边处,要有一圈和衣服同色系、但更深一个色号的滚边。
比方讲,一套紫色碎花睡衣,它的滚边一定是深紫色。要是男士穿的蓝色睡衣,就会镶一圈深蓝色滚边。
碎花一套头、两只口袋、深色滚边,这三大元素一碰撞,就构成了睡衣的鲜明特色。
当然,最关键的是,这种可以穿上街的睡衣,夏天款的里面肯定有内衣裤,冬天款的还有棉毛衫、棉毛裤做内衬。
其实,它更像是一种“内衣款外出服”,好比电影里超人外穿的内裤。
爱穿睡衣出门的阿姨爷叔们为自己辩护时,也会以此为论据:“阿拉睏衣里厢是有内衣裤的。那种露肩胛露大腿的吊带衫超短裙,就更加雅观吗?”
长辫子老爷叔
不仅睡衣里有内衣裤
睡衣外又套了背心、围兜
在阿姨爷叔们看来,“睏衣”只是个名称而已,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?
“上海人的‘睏衣’和欧美人的睡衣完全是两回事。”马尚龙说。
“西方人的睡衣里面是没有内衣的,材质透明飘逸。晚上洗好澡穿上,喝喝红酒看看书。 ”
“而上海人的睡衣是一种多功能衫,用途广泛,既能居家,又好外出。 ”
那么上海这种可以外出的睡衣是怎么诞生的呢?
这与上海特有的弄堂生活息息相关。
1955年出生的刘晓兰(化名)从小生活在上海老城厢——老南市区的小南门一带。
“我小时候从来没在马路上、弄堂里见到过睡衣。印象中睡衣是一个只会出现在电影和书本里的东西,高档洋气,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不搭界。”
“到了七八十年代,经济条件一点点宽裕起来,弄堂里开始有人穿着碎花式样的睡衣出入。”
“最开始穿睡衣出门的人,脸上还有几分显摆的意思。在那个年代,穿睡衣还算蛮时髦的一件事。”
刘晓兰说,后来穿睡衣出门变得越来越普遍,弄堂口、菜场里总能看到一些阿姨,穿着一身睡衣,头发卷得出奇地高。
“一些邻居会自己用缝纫机做睡衣。看上去蛮随意的,实际上衣服的细节上有很多小心思,比如点缀蕾丝花边,用布店里最新款的料子。”
襄阳南路上
穿着成套睡衣的
上海爷叔
马尚龙认为:“睡衣的流行,和七八十年代期间,上海市区居住条件紧张有很大关系。”
“当时一栋石库门里起码要住七八户人家,但厨房间就一个。”
“不管你住两楼还是亭子间,每天都要去厨房间好几趟,随身还要带着钥匙、火柴、零散钞票,有两三个袋袋的睡衣最实用。”
“在家里,没有人舍得穿上班的衣服去烧饭,但如果只穿着汗衫短裤进出厨房,又太不雅观,经常还要下楼到弄堂口买买小葱酱油。”
“睡衣打破了空间不断转换带来的尴尬,是名副其实的居家、外出两用衫。”
“刚开始,上海人自己把旧衣裳改成宽松的‘睏衣’。等条件好点了,商店里就能买到了。
这样一来,弄堂里进出的人既避免了尴尬,还能维持一点体面,作为弄堂串门的着装也亲切。”
对上海人来说
弄堂是半私密的空间
没必要穿得一本正经
睡衣不仅适用于弄堂生活,在最早的工人新村,也是派大用场的。
“当年的‘两万户’基本上都是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间。睡衣既然能穿去厨房,也就好穿着去买小菜。”
“到后来延伸到公交车上、电影院里,只要不是上班这类正式场合,都被睡衣慢慢覆盖了。”
大城市、小弄堂,为睡衣登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。
从小生活在永嘉路一带弄堂里的陈妍廷说,如果自己在马路上看到睡衣,首先会想到,对方肯定和自己一样,就生活在衡山路周围。
“因为你穿着睡衣,活动范围总归在一公里内,不大会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。”
对于睡衣与空间的关系,“知乎”上也有网友曾这样调侃:“不是住上海市中心的人,有那闲情穿个睡衣去黄浦江边看夜景么?”
上海人喜欢穿睡衣出门3
去过上海的朋友们,一定不会忘记大街上穿睡衣的男男女女们。
他们昂首阔步,旁若无人,穿梭在各大超市、菜场,甚至南京路的街头。和他们擦肩而过的,还有穿着最入时的上海摩登男女们——恐怕没有比这更魔幻现实主义的画面了。
上海向来走在时尚潮流的最前沿,这里的人们在穿着打扮上绝不松懈。可也是最体面的上海人,把不甚合身、还印着迷之花纹的成套睡衣,大大方方穿出了家门。
2009年10月30日,上海,身穿睡衣的大叔骑着电动车现身街头。
早在世博会的前一年,上海市政府为整顿市容,就提出“睡衣睡裤不出门”的倡议。各大小区纷纷动员志愿者们,在小区门口劝导穿睡衣出门的市民。但是,不少上海阿姨们并不买账,不忘回上一句:“侬鼓力嘎多咧!(你管得太多啦!)”
那么,上海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穿睡衣上街?这一习惯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?
都是弄堂惹的“祸”
其实,民国初期的上海,就有穿睡衣出门的人了。不过当时只有两种人这么干——大财主和舞女。大财主在家门口以睡衣示人,显示自己不仅有钱,还很闲。毕竟睡衣是舶来的洋货,普通人家是负担不起的。舞女们则在白天穿睡衣示人,表示她们此时不做生意。
倘若此时谁有了件睡衣,拿出来显摆还来不及,怎么会藏在家里穿呢?所以,普通人不穿睡衣出门,不是因为不好意思,而是根本买不起。
民国时期的上海人,虽然大部分都住在弄堂里,但是彼此阶级差异巨大。资本家、中产阶级和中下层居民,住的房子都是不一样的。
2008年7月23日,上海,南京西路与吴江路之间的老石库门弄堂,狭窄而拥挤。
最早的石库门弄堂,本是土豪乡绅们住的地方。19世纪60年代,太平天国起义把江南地主豪绅赶进了狭小的上海租界,使得租界人口暴涨几十倍,催生了旧式石库门弄堂。民国以后,这些有钱的绅士们逐渐搬出石库门,改住新式里弄,淘汰下来的石库门弄堂渐渐变成低档住宅。
20世纪30年代,日军占领上海,租界再一次成为战争避难所。大批居民涌入租界,房地产商乘机将已被淘汰的旧石库门弄堂出租,很多承租户也将原来独门独户的单元分房间出租。破败的石库门弄堂很快拥挤不堪,住着大量中下层居民。
虽然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如中等收入群体住的新式石库门弄堂,更比不上资本家的花园弄堂。但能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市区寻得住处已属幸事,何况还能享受自来水和煤气的便利。
但由于一户单元要分租给好几户居民,这些便利的设施都需与人共用。由于并没有独立卫生间,洗澡可能扯一条布帘就完事。诸如洗漱、淘米、洗菜、做饭之类的日常生活,都要在弄堂里进行。
2013年7月2日,上海城隍庙边的一条老弄堂,房子里接出了莲蓬头,孩子坐在大脚盆里冲凉洗澡。
原本作为公共通道的弄堂,逐渐成为家居空间的延伸,甚至被居民们归为私人空间的一部分。因此,对于分租共用的中下层居民们,在卧室里穿的衣服,在弄堂里穿自然也没关系。
怡德里弄堂口,一位身穿睡衣的大叔坐在木椅上休息。
但是,正如此前所说,民国时期的普通人是买不起睡衣的。睡衣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成为潮流,被上海人穿出了家门。那么,睡衣又是如何走出弄堂,走上大街的呢?
如果弄堂只是作为私密空间的延伸,睡衣自然不会出现在绝对的公共空间——比如弄堂外面的大街。可是老式弄堂往往处在市中心的热闹地段,许多机构和店铺迫于高昂的.房租,不得不搬入弄堂。
弄堂里多的是钱庄、洋行,旅馆、浴室、饭店也很常见,至于小杂货店和小食品店,就更不值一提。由于商业活动兴盛,以弄堂为中心形成了不少交易市街。如今你在上海会馆街看到的潮州、漳泉、商船会馆,就是当年弄堂繁华商市的见证。
上海弄堂里如今还在营业的前进旅馆。
因此,虽然围墙和大门给了弄堂居民私密和安全的感觉,但齐全的商业功能使得弄堂成为面向城市开放的空间,里弄街区也作为城市里四通八达的隐形脉络而存在。如此一来,弄堂作为个人私密空间延伸的同时,又有城市公共空间的强烈渗入。
在弄堂里能穿的睡衣,在其他不太正式的公共空间自然也能穿。穿睡衣的弄堂居民,去沿街店铺打油买米,再走向稍远一点的菜市场和超市,也成为稀松平常的事情。
上海老城区里弄里的早餐店,有的居民穿着睡衣、趿着拖鞋就跑来吃早饭。
总的来说,狭窄的居住空间和分租共用的模式,再加上弄堂承担的公共空间功能,使得弄堂居民把睡衣穿出家门,走上了大街。
“体面人”也得这么穿
但是,建国以前,这种分租共用的模式并不普遍。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37年发布的报告,全部弄堂中有40%依然是独门独户,享受这样宽松居住条件的,大多为中等收入群体,而三户以上人家合租的房屋只占44%,不到一半。
直到建国以后,分租共用的居住模式才逐渐成为跨越阶级的普遍现象。
1949年建国以后,弄堂房屋的所有权发生很大变化。1955年的公私合营制度变相充公了绝大部分的上海私有住宅,大洋行、大公司的房产都划归政府所有,由房管所统一管理,以低租金租给无房户居住,原来独门独户的住宅普遍住进了多户人家。
张锡昌在《弄堂怀旧》里提到,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明月里弄堂,每一幢房子差不多都住一户人家。解放后,家住五号里的王先生被查出有汉奸嫌疑,全家搬走,原来的房子被分配住进了五六家人。
2002年,上海里弄, 里弄里有读报的、洗衣的、刷马桶的、生火的,整个一幅生动的上海市民图。
另外,原先一些中小私人产权的住户,在动荡时局中收入不稳定,只好将独户居住的单元分租给外人。在房屋重新分配的过程中,多数住宅单元都挤进两个以上的家户,过去在中下层居民被迫经历的分租共用,成为弄堂居民的普遍境遇。
而在弄堂以外,国家为缓解上海居民“住房难”的问题,开始修建工人住宅和居民新村。考虑到国家财政状况,本着节约空间的原则,在曹杨新村、空江新村之后建设的二万户公房,均未设计独立厨房与卫浴,由一单元的十户居民共用一套。
始建于1953年的崂山新村,是上海市政府在解放后建造的二万户公房之一,在高楼大厦间俨然是“城中村”。
与此同时,国家实行计划经济,各类生活必需品凭票供给。官与民、穷与富、身份或职业的不同都逐渐接近和靠拢。在分租共用的居住条件下,生活习惯在合租者面前一览无余,人们慢慢学会隐藏自己的阶级标识,不轻易暴露。而物质条件的困窘也迫使人们放弃原有的生活方式。
红木衣橱要丢掉,大鱼大肉不能做,旧有的着装礼仪和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松动。穿睡衣在弄堂里走动,对于中等收入群体来说,也不再是“不体面”的事情。
2010年04月06日, 穿着花睡衣的女人,脚踩一双还算精致的皮鞋,刚刚购物回来,穿过弄堂。
由此,过去中下层弄堂居民的生活经验,逐渐被各个阶层分享,成为普遍现象。本来在家里才可以穿的睡衣被合理化为家居服,再逐渐向洗手、上厕所之外的串门、借葱借蒜等行为扩张,然后走出家门,上下楼梯,最后走出社区。
虽然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居民共同经历着分租共用的居住生活,但是穿睡衣出门似乎并没有引起关注,也不会被当作一种独特的现象。事实上,直到70年代末期,穿睡衣上街才成为一种潮流。
2016年的秋冬上海时装周,睡衣亮相街头,作为潮人街拍的元素。
其实,并不是五六十年代没有这种现象,而是因为改革开放前,城市居民做衣服都要凭布票,定额很少,做专门的睡衣是很奢侈的事情,很多都用旧衣服裁剪而成。
当布票制取消,睡衣作为常见的商品进入市场流通后,人们从单调和拮据的布料中解脱,纷纷将色彩艳丽的睡衣穿出家门,睡衣上街此时才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,成为上海市民的文化名片。
不穿反而不习惯
改革开放后,上海人狭窄的住房空间并没有得到很大缓解,弄堂依旧是城市居民住宅的主力。虽然商品化住宅逐渐增多,但截止1997年底,生活在上海各式里弄中的居民总数仍有317万,占市区人口总量约40%,而在80年代末,这一比例曾超过60%。
与此同时,弄堂生活的便利性也没有消失,人们穿着睡衣,不用过马路,就能在街区商店买到绝大多数日常用品。

文档为doc格式